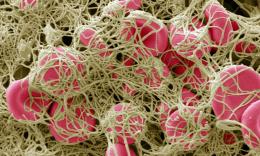文:Sally Adee
译者:Sally Adee
来源:译言网(yeeyan.org)
原文标题:Stupidity: What makes people do dumb things
人类的智力千差万别。为什么进化没把大家都变成天才呢?又为何高智商的人也会犯傻呢?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曾写道:“地球有边,但人愚则无界”,他几乎为此抓狂。在致路易丝·柯蕾(Louise Colet,小说《包法利夫人》的灵感出自这位法国诗人)的多封信中,福楼拜对其愚蠢同行淋漓尽致的谴责,比比皆是。从中产好管闲事者的说长道短、到学术界的讲演,他到处见到愚行。甚至连伏尔泰都难逃其法眼。痴迷于此,他把晚年倾注于编纂一种愚行百科全书,收集了几千个范例。惜巨著未成身先死;有人认为,福楼拜58岁猝死,与编写此书受挫不无关系。
记录人类愚行的林林总总,也许本身就徒劳无功,这或可解释人类智能研究倾向专注智力范围高端的原因。然而,智力范围如此宽泛,带来了许多引人入胜的问题。
例如,既然聪明有那么强的优势,为什么我们的智力却不一致呢?
还是智者也有软肋能让愚者得手?
再就是,绝顶聪明的人为何也会犯傻呢?
现在发现:通常的智力标准(特别是智商IQ)与令福楼拜愤怒不已的非理性、不合逻辑的那类行为基本没有关联。一个人可以智力极高而同时极其愚蠢。弄清导致智者做出不良决策的因素,正在开始揭示许多最大社会灾难的成因,包括近期的经济危机。更有趣的是,有一种可困扰每个人的误区,最近的研究也许能为我们指点迷津。
令人惊讶的是,把智能与愚蠢简单当作一个范围中两个极端的观点,仅是现代才有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神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所描绘的《愚蠢女神》(拉丁文是Stultitia)自成一个实体,是财神与青春仙女之后(见附图一);其他人则把愚蠢当作虚荣、顽固、仿效的结合。据有多本讨论愚蠢专著的荷兰历史学家Matthijs van Boxsel说,只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愚蠢才与智力平庸混为一谈。他说:“那时,布尔乔亚大权初握,理性与启蒙成了新的圭臬。这让每个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现代研究人类能力差异的尝试,倾向于专注智商测试(IQ),以单个数字来概括某人的脑力。据密歇根大学Ann Arbor校区的心理学家Richard Nisbett说,这些测试也许不过是抽象推理能力的度量。“IQ值120,微积分不成问题。100分,你还能学会但需要有动力、下大功夫。假如只有70分,掌握微积分无望”。该指标看来能够预测学业和专业方面的成功。
智商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大概我们智力方面三分之一的差异取决于成长环境,例如营养、教育。而基因则决定了二人智力差异的四成以上。
这些差异也许会在大脑中的神经连接中显现。较聪颖的大脑神经细胞间的网路连接更高效。据位于Bristol的西英格兰大学的心理学家Jennie Ferrell说,这也许决定了某人使用 “工作”短期记忆来连接无关联的各种主意、快速获取解决问题策略的能力大小。“那些神经细胞连接是建立高效智力连接的生物学基础”。
智力的这一差异令某些人想弄明白脑力高超是否有代价,否则,为什么我们没有都进化成天才呢?很不幸,证据不足。
例如,有人主张:较机智的人也许患抑郁症更多,导致较高的自杀率,但没有研究得以支持这一观点。仅有的反映智力不利一面的研究之一,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智商较高的士兵死亡的可能性更高。然而,其影响微弱,也许有其他因素扭曲了数据。

01
智能荒原
另外一种解释是,智能差异也许起源于在人类文明驱动大脑进化挑战减弱之后的一个名为“遗传漂变”的过程。斯坦福大学的Gerald Crabtree是这一观点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指出,人类的智力取决于约2000至5000个不断突变的基因。在远古时代,那些具有使其智力下降突变基因的人来不及把基因传下来;但Crabtree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协作,脑子慢的人可以搭乘智者成功的顺风车。他说,公元前1000年的某人假如生活在当今社会,也会与“我们同事和伙伴中最出类拔萃者不相伯仲”。
这一理论经常被称为“蠢人统治”(idiocracy)假说,源自同名电影,该科幻片想象未来的社会安全网造成了智能荒原。尽管这个理论有些支持者,但证据不牢固。我们很难估算远古祖先的智力,而近代人类的平均智商实际上有些许上升。英国约克大学心理学家Alan Baddeley说,这一事实至少证明了:“害怕智力较低者繁衍更多造成全国智商下降,是没有根据的”。
无论如何,近期的发展,也许会令这些关于智力进化的理论需要大规模修正,已经使许多人推测:人类思维还有比智商更多的维度。批评者早就指出过:IQ得分很容易被某些因素曲解,如:阅读困难、教育、文化等。
Nisbett说:“如果智商测验是18世纪苏族印第安人设的,我多半会考得一塌糊涂”。
另外,得分80的人仍能讲多种语言,一个英国人甚至还能参与复杂的财务诈骗。
反之,高智商并不能确保某人会理性行事,例如某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坚持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骗局。
正是这种权衡证据、明智决策能力的缺失,使福楼拜气愤填膺。但与该法国文豪不同的是,许多科学家对愚蠢本身避而不谈,Baddeley说,“这个术语不科学”。然而,福楼拜认为深度罔顾逻辑会困扰最聪明头脑的观点,正在得到重视。研究情感和智力的心理学家、作家Dylan Evans说:“有些愚蠢的智者”。
什么能解释这一明显的悖论呢?
有个理论来自Daniel Kahneman,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认知学家,以研究人类行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过去经常假定人天生是理性的,但Kahneman及其同事Amos Tversky发现并非如此。他们发现,当我们处理信息时,大脑可使用两种不同的系统。IQ测验仅能衡量其中一种,即在有意识问题求解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审慎处理方式。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默认的方式却是使用直觉。
首先,这些直觉机制给予我们进化上的优势,提供了认知上的捷径、有助于应付信息超载。这些包括认知偏见,例如墨守成规(stereotyping)、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抵制含糊性(resistance to ambiguity),即易于接受首个解决方案,即使它明显不是最佳方案。
尽管这些被称作“启发式方案”的成型偏见也许在某些场合有助于我们的思维,但是,对其盲目接受则会令我们误判。为此原因,无法识别或抵御它们是愚蠢的根源所在。Ferrell说:“大脑没有一个开关告诉我们‘我仅将餐馆定型化、却不涉及人’。你必须训练那些肌肉”。
因为愚蠢与智商无关,真正弄懂人类的愚蠢则需要另一种测验,检查我们是否易被偏见左右。一个候选测验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认知学家Keith Stanovich,他正在研究“理性商数”(译注:rationality quotient,简称“理商”或“RQ”),以测量我们超越认知偏见的能力。
考虑下列检测“含糊效应”(ambiguity effect)问题:
杰克正在看安娜、但安娜正在看乔治。杰克已婚,乔治则未婚。据此请回答:有无已婚者正在看未婚者?可选择的答案有三个:“有”、“无”、“无法确定”。
绝大多数人会选择“无法确定”,只因为这是首先想到的答案,但缜密的推理可证明答案应该是“有”。
RQ也能度量风险智能(risk intelligence),用于定义我们对某些概率可能性的校定能力。Evans说,例如,我们倾向于高估赢得彩票的可能性,而低估离婚的可能性。风险智能低,能令我们不知不觉地选择错误。
那决定我们自然就有高RQ的是什么?Stanovich发现,与IQ不同的是:RQ并非根源于基因或者孩提时期的教养因素。
RQ最取决于“元认知”(metacognition),即评估自己知识的有效性的能力。具有高RQ的人已经采取了增进这一自我意识的策略。
Stanovich说,一个简单的做法,是找到一个问题的直觉答案,再考虑其对立面,然后才最终决策。这帮你培养出敏锐的意识、了解自己所知与所不知。
但即使那些天生就具有高RQ的人,遇到不可控情况时也难免中招儿。Ferrell说:“你作为个体可能具有极强的认知能力,但难抵大势所趋”。
如同你可能经历过的,感情干扰最可能导致出错。悲痛、紧张等感觉搅乱你的工作记忆,使你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穷于应付,你只能退而求次,采用启发式作为捷径。Ferrell说,这也许可以解释更多的持续经验,如“成见威胁”(stereotype threat)。这种焦虑,少数群体在他们意识到其表现可能被用来强化现存偏见时会经历到;已被多次证明会降低测验得分。
André Spicer和Mats Alvesson发现,某些行业也许是最鼓励愚蠢的。在他们得到这个发现时,二人对愚蠢并没有兴趣。伦敦卡斯商学院的Spicer和瑞典隆德大学的Alvesson计划调查的是一流机构如何管理高智商成员。但很快他们就不得不改变初衷。
同样的模式一次又一次地显现:某些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公关代理行、咨询公司)愿意聘用高资质的个人。Spicer说,然而,非但这些专长没有得到利用,“让我们惊讶的事实是:恰恰是他们的专长立即被停用”,他们把此现象称之为“功能性愚蠢”(functional stupidity)。
他们的发现,结合偏见和理性来看,是有意义的。Spicer说:“起初我们没有把Kahneman的理论看作是我们工作的基础。但很快我们就开始注意到与其实验室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有趣关联”。
例如,机构的惯例是关闭雇员的风险智能。
Spicer说:“其所作所为与结果没有直接关系”,故无从判断行为带来的后果。企业压力也强化了含糊性偏见(ambiguity bias)。
Spicer说:“在盘根错节的机构里,含糊性司空见惯,企图不惜代价避免含糊性亦然”。
其后果也许是灾难性的。在去年一次元分析(meta-analysis)中,Spicer和Alvesson报告说,功能性愚蠢是促成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因素(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9, p 1194)。
Spicer说:“这些人聪明非凡,都知道抵押贷款支撑的证券和结构性商品有问题”。但是,不仅谁都没有责任关注这些问题,雇员提出担忧反而会面临纪律惩罚,似乎是因为他们挖了上级的墙角。结果是本来可以大显身手的雇员抛弃了逻辑思维。

02
愚蠢的共和国
从经济崩溃来看,上述发现似乎确认了福楼拜关于大型群体中愚氓能量的某些恐惧,他将其讥之为“愚蠢共和国”。它还证实了van Boxsel的部分观察,即高智商者的愚蠢最危险,这是由于他们经常被给予重任,“他们智力越高,其愚蠢后果的灾难就越深重”。
据Stanovich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多年来”金融界一直极力要求有个良好的理性测验。目前,RQ测验不能像IQ那样给出确切的得分,因为需要比较大批志愿者,才能研制出稳定的范围、得以比较不同的群体。然而,他已经发现:仅仅接受这类测验即可改善我们对普通启发式方案的觉悟,有助于我们免受启发式的诱惑。在John Templeton慈善基金会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经费资助下,今年一月他启动了项目研发该测验。
有没有人来完成福楼拜未竟的事业,则是另一个问题。以愚蠢为主题的第七部著作付梓之后,van Boxsel将不再继续。但是,通过决定把全世界每条推文(译注:tweet,即Twitter中的每一条短文,类似一条微博)归档,美国国会图书馆已经(也许是不知不觉地)接过了接力棒。
对其他人来说,知晓我们愚蠢的本质,可能有助于我们摆脱其掌控。也许文艺复兴时代的哲人如伊拉斯谟充分理解了愚蠢统治我们的能力。《愚蠢女神》画像之下写着“愚蠢控制我”,即是明证。
—The End—